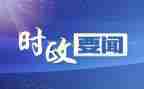读一本书后我们对书中的主题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和读后感,这本书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读后感,365文档网小编今天就为您带来了远山淡影读后感8篇,相信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1
一本很像散文的小说,主人公兼叙述者悦子的大女儿景子自杀后,她的小女儿妮基前来看望劝慰她,与她共同居住了5天,这5天内,悦子时不时回忆20年前的一段往事,出人意料,这段往事表面看来只是悦子的朋友佐知子与其女万里子的母子往事。
二战后的日本,佐知子失去了丈夫,客居丈夫的伯父家,而她一心向往美国,以期改变生活。但是她的女儿却想居住在伯祖家,而且对妈妈选中的美国男子十分鄙夷。后来,佐知子无法承受伯父家的沉闷空气而搬离其大宅院,暂居在其长崎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木屋中,等待那个美国男子寻觅机会带她母女移民美国。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前往美国的计划都成了泡影,佐知子却还在傻傻地等待。这期间佐知子口口声声说前往美国是为了女儿,可是对于她的女儿的生活、心理、诉求她的表现却是漠视的,母女关系是疏离的甚至矛盾重重的,矛盾的激化就是面对又一次前往美国的计划,佐知子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坚决溺死了女儿深爱的小猫咪。她们的故事就此结束。后来怎么样悦子就不再回忆了。
作为叙述者的悦子,二十年前,刚刚怀孕,其丈夫工作正处在上升期,其公公曾是中学校长,对待子女还是比较开明慈爱的,那时她一心期待孩子的降临,对万里子表现出了关心呵护。可是后来她却移民英国。发生了什么事导致她移民、怎么移民、移民后怎样……文章没有交代。只是说,移民后她的女儿景子很幽闭,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大女儿自杀下葬后、二女儿来看望她时,二十年一个夏天的往事,断断续续地在悦子脑海、心田、梦中不断沉渣泛起。这就奇怪了,自己的女儿死了,悲不自胜,为什么以别人为主人翁回忆往事呢?
细心的读者,才能发现,原来,现在的悦子就是过去的佐知子,自杀的景子就是过去的万里子,而过去的悦子是不被生活裹挟的理想化的“佐知子”。战争,抑或想逃离现状的欲望,夺取了佐知子的优雅贤惠,所以在万里子的思想中,有个母亲死在水中了,在小木屋的对面一直有个他人看来不存在而万里子却确信存在的女子存在,而在佐知子看来这只不过是万里子的幻想罢了。面对女儿的自杀懊恼不已的悦子,自然反思自己的责任,可是她却难以直面这样的结果,所以借助别人的故事,深挖了自己种的恶果。作者真是高明。
战争,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二战作为跨国战争,还激荡了一些人的思想。贵族夫人藤原太太,丧父,失子,富足高贵的生活也灰飞烟灭。面对如此悲痛,藤原太太,放下身段,抑制悲伤,开了小面馆,自给自足,还时不时鼓励他人要积极乐观,在佐知子生活陷入困境时,还接收她来打工。这是母辈面对意料之外的困境的处置方式,这种处置方式无疑是作者肯定的。
佐知子,失去了丈夫,丈夫的伯父愿意收留她们母女,伯父家有大大的院子还有仆人,可是安逸的生活,在佐知子,却是沉闷的寂寥的,人生没有希望的。她向往美国,觉得只要到了美国,有的是希望,有的是机遇,就会有不一样的有意义的人生。佐知子的父亲打开了佐知子的世界之窗,可是战争却关闭了佐知子走向世界的门。面对这样的打击,佐知子没有听天由命,她选择一个美国人作为她前往美国的路径。可是这个美国人,甚者在睡室里解决大便,所以在万里子看来,他只不过是个酒鬼,是个懒猪。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计划带她们母女去美国,但总是在最后时刻,不辞而别,他甚至花光了佐知子的积蓄。小孩子万里子都懂得这样的男子靠不住,可是佐知子却对其坚信不疑,耐心去等待。面对创伤,佐知子选择逃离现有环境,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可是她却把开启新生活的砝码错误地压在了一个不可靠的人身上,她一心只想着移民,忽视了与女儿的沟通交流,乃至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女儿。
即便成功移民,就真的能够融入到异国生活乃至文化之中吗?悦子的小女儿妮基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她只习得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真正地开启自己正常的人生。在和母亲相处的五天中,她的生活状态也慢慢地展现,和其姐姐景子没有感情,没有工作,和男友同居。景子、妮基的结局与现状无声地对佐知子的选择做了回答:错。
控诉战争是作者的一个思想,思索日本女子的出路也是题中之义;如何处置母子关系,读者可以以文中的几组母子关系为镜,进行深入思考;时代变更中,众多思想纷纷萌芽发展,身处其间的大众,何去何从,读者自行考量。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2
人生中第一次体验绿皮火车,经历长达24小时的卧铺的时候,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像白开水那么清澈却让人细思极恐的书。
这是诺贝尔得奖者石黑一雄的处女作,看完之后我大为惊讶,第一本书就写得如此巧妙用心,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故事编织得看似无意其实是在估计出错的细节中告诉我们内心泛起的涟漪。
全书分两条线索不停插叙,用第一人称描述了女主角悦子的回忆,由于悦子在现实里做了令人遗憾的事情,她一直在逃避,欺瞒自己,在她的回忆中,有一位叫佐知子的女性,佐知子的行为乖张,和女儿矛盾不断深化。刚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甚是混乱,像是粗心的作者把回忆与现实混淆,慢慢觉得假象横生,读到一半,竟觉像悬疑小说、恐怖小说。
作者描绘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二战后的日本,丈夫参军牺牲留下的遗孀悦子为了更好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国,初心是为了女儿有更好的未来,但是女儿偏偏不适应,悦子在母女的.矛盾中发现,其实移民最深处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的自私,所以对女儿的不适应视而不见,甚至自我麻木,最后女儿自杀吊死在树上。悦子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伤痛和愧疚,女儿(景子)自杀只成为了她不断重复的一个噩梦,甚至连自己都相信这种事情不曾发生。
在从日本移民到美国前的一段时间,她的女儿曾经反抗过,但是她沉沦在自我笃定中,而在书中也并非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回忆来呈现,而是说“在十年前,曾经有个叫佐知子的女士让我走进了她的心里……”然后以第三人称去对佐知子(其实就是悦子本人)和女儿万里子(其实就是死去的景子)的矛盾,移民前和伯父家人的争执等等。
对于一个母亲,女儿上吊自杀恐怕是最难接受的,何况女儿的悲剧与自己有很大干系。在悦子的回忆里,有很多意象与此相关:万里子看到一个女人溺死婴儿,读后感佐知子当着女儿的面溺死女儿心爱的小猫,一个小女孩被发现吊死在树上……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佐知子(悦子)有没有想过像溺猫、那个女人溺婴一样溺死万里子(景子)?
作者在编织着两条其实为一条线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看到一半,任何人都会隐隐约约感受得到悦子和佐知子就是同一个人,于是带着侦探一般的探索和疑问不断得在书中寻找蛛丝马迹,所以后半本书我相信任何读者都会读得极快,而且神经紧绷,就像看悬疑小说一样,希望看到结局,看看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
可是偏偏直到故事的最后一个字,悦子都没有坦白一切,依然用佐知子这个身份给自己做掩饰。直到后记,作者才坦然公开真相,佐知子就是悦子本人。心理学上,我们出于内疚和忏悔,出于痛苦至极而不愿面对,就会用一个故事和虚幻来掩饰真相。在大量研究发现,尤其在采访一些受难者或作恶者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用第三人称来道出别人的故事,一方面来掩盖自己的羞耻,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这是他们内心真真正正因为羞愧想要忏悔的体现,于是触发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转移”和“象征”的心理防护机制。“我就觉得用这种方法写小说很有意思:某个人觉得自己的经历太过痛苦或不堪,无法启口,于是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自己的故事。”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3
模糊,吊诡。
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示,一抹淡影。读完整部书,给人的感觉就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给人以朦胧的感官。初拿到这本书,颇读出了几分不知所云,本书共有三个时间线,每一条线相互穿插交错,似是有所关联,又无法切实说出它们的纽带,书中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一旦看到一个重要的事件,想追究其缘由时,章节戛然而止,开始跳到另一时间线讲述一些“毫无关联”的故事。每当这时候,心中总会生出几分如鲠在喉的郁气。直到看到最后,全书终止,所有时间线收束在一起,也还是留下了大片大片的空白,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收集微小的信息,来一点一点地拼凑,自己构建出这本书隐隐让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观。这时,我才姑且放下对作者满满恶意的执念。
一个日本女人悦子寡居于英国,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景子是日本血统,小女儿妮基则是与英国丈夫生的日英混血。故事就是从大女儿自杀后,小女儿从伦敦赶来陪伴母亲开始的。在这时,悦子回忆起了几十年前在战后刚复兴时,在长崎遇到的一对母女——佐知子和万里子。
佐知子和万里子是一对略显奇怪的母女,佐知子是一个身处流言蜚语之境的女人,万里子,性格孤僻乖戾,与母亲关系疏远。也许是出于一种复杂的心理,悦子开始主动向佐知子搭话,介绍她去藤原太太的小店帮工。在一来二往的交流中,二人关系日渐亲密。在这段悦子的回忆中,她“扮演”的是一个克己守礼,恭顺贤良,并即将迎来自己的孩子的的妻子身份。而与之相反,佐知子是一个向往美国生活,厌恶旧日本,急于脱离现状,急于改变的女人,为了她的美国梦,她搭上了美国男人弗兰克,想弗兰克带着她们母女去往大洋彼岸,在她的眼中,一味安逸的伯父家和她那“不知进取”的安子表姐只是一座有无数空房间的坟茔。对于这个离开日本的决定,佐知子反复强调“我是个母亲,我女儿的利益是第一位的”“万里子在美国会过的很好的”“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但万里子不愿意去美国,她更渴望的是在安子阿姨家稳定的生活,而不是将自己的未来,拴在一个“像猪一样撒尿”的美国酒鬼身上。虽然佐知子口口声声是为了女儿,但实际上,去美国这件事应该更切合佐知子自己的利益与愿望。这样的矛盾之中,在之后佐知子淹死小猫的事件发生后,她们的紧张的关系达到了高潮。
看到这里,悦子和佐知子,景子和万里子之间好像更有了几分若有若无的牵连,这种模糊的界线在最后悦子和妮基的谈话中终于破碎。“那天景子很高兴,我们坐了缆车。”全文构建的那个朦胧的世界轰然崩塌——佐知子就是悦子,万里子就是景子。悦子通过自己扭曲的回忆,将自己的狼狈与罪恶掩埋在别人的故事里,妄图藏在名为“别人”的面具里苟延残喘,直到最后,她放弃了自己的伪装,将自己的虚伪,和内心深处朦胧的一个自己曝在阳光之下。
本书作者石黑一雄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佐知子,也许就是悦子“恶”的情感的外化,她将自己的善恶剖离出来,在回忆的世界里自欺欺人,最后,与自己的善和恶共犯沉溺。
本书克制、清淡,拥有浓郁的日式风格。所以说,悔恨是你的,宽恕也是你的,隐藏在远山中的罪恶终会淡去,只留下回忆投映在岁月里,淡淡的光影。
“我笑了笑,朝她挥挥手。”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4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爱好者,也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所以我对文学界的事情并不是很熟悉。例如,石黑一雄先生,虽然他获得了布克奖,但直到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我才知道这位日本英国作家。对于日本作家来说,我很惭愧,我没有读太多,只有大江健山郎先生,他的性人、万延元年足球队和空翻我读过,巧合的是,他是另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人。然而,与其他日本作家的作品相比,大江先生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即他的文学中有很强的主义色彩,这与昆德拉、萨特和加缪非常相似。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我个人认为,虽然中日之间的地理距离非常相似,但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随着这个过程,三种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所谓的三种观点,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来说,不仅仅是抽象和空洞的理论,更不用说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一个民族和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建立秩序,甚至影响他们对世界、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和个人情感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是看日本动画长大的,但我对日本文学家在具体写作中对人物情感、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描述非常陌生,但江先生的作品是个例外。
听说石黑一雄先生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不禁对他感到好奇。他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三大移民作家之一,那么他的思想和写作是更接近英国人,更接近日本人,还是处于疏远状态呢?
人们总是很难疏远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和文化传统。他经常受到后者的影响,比他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因此,石黑一雄先生被认定为“移民作家”。“移民”这个身份意味着你总是离开你的家乡,但很难完全摆脱它,因为“而起源,保持未来”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你总是有移民国家的东西“他者性”,无论是来自他人的文化、他人的视角还是他人的情感模式。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总是我们要处理的对象。在当今世界,事物本身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如何呈现给我们每个人的,它会引起什么样的情感,以及如何出现在这样的情感、变形和转变中。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5
简单的故事情节,甚至鲜有冲突和波折,就在轻描淡写中,石黑一雄就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空背景中的几个人物刻画的生动、鲜活和深刻。
区别于其他作品描写战争对人类摧残的血腥与残暴,只是区区几点暗示的背景点缀,却让人更能感到那种令人窒息,深入骨髓的压抑与伤痛。
战争让名门闺秀的佐知子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让她流落在她所唾弃的生活环境和邻里环境中,只能不断欺骗自己通过一个只会玩弄她的美国醉鬼让她摆脱困境重燃美好生活的假象,这些失去也让她变得冷漠甚至残忍,她淡定的试图淹溺小猫的场景是多么的令人寒意顿生,而她从伯父家带走(偷走)精美茶具也把她的品味追求描写的多么栩栩如生。
万里子阴郁、多疑、任性、执拗、不能像同龄人一样去学习,也没有一个朋友,面对对她甚至都冷漠的母亲,生活里可以说没有一丝色彩。可是她爱好美,她喜欢画画;她渴望友情,陪伴着她的小猫;或者她掩藏的充满着爱,她也试图去取悦于母亲,当看着被母亲淹死的小猫时,她的无助、痛苦又是何等的撕裂。
第一人称的悦子是一个富有爱也被爱着的人,她可以给素不相识的佐知子以无私的帮助,她被绪芳先生所解救也无微不至的疼护着绪芳先生,她热爱生活,喜欢杜鹃花,她善良,甚至要特意停下脚步放误入油灯的昆虫出来,她包容,小心呵护着她两人丈夫,和两个一个热烈一个阴沉的女儿。
还有热爱着祖国与传统却被时代抛弃的绪芳先生,身居高位的遗孀却放下身价重拾生活的藤原太太,难以走出痛失爱人阴影的藤原儿子,一心努力争取生活却惨遭不幸的二郎,包括一直悲惨自杀却始终未出镜的景子等等都诠释了在那个背景下丢了生活却又重拾生活的人们的纷杂场景。
人,有的时候很脆弱,包括肉体,可能为疾病、意外、战争所摧毁,支离破碎。
人,有的时候很坚强,比如精神,卑微或高贵,平淡或热烈,总是在那,描述着人本身。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6
石黑一雄也没逃出亚裔作家卖弄母国文化的怪圈,灵感来源于侨胞难民的口述,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只在最后章一个微小细节点醒了读者,“我邻居”就是我。
作为石黑一雄的处女作,独白式的叙事和作品立意都与后来的作品有很大的差距。
叙事线很单调,佐知子和万里子在日本盼着去美国做美国人,景子和“我”在英国一个抑郁自杀,一个搞不懂混血女儿妮基已经西化的生活和思想。
景子的自杀让“我”想起了出国前颇为不堪的过去,“我”只能借由佐知子的身份回忆起景子从一开始对移民的反抗情绪。同时,佐知子也在不断为自己辩解“是为了女儿”“女儿的前程”。最后回到现实中时,“我”的心理防线的崩溃便是忆起景子最开心的一天。
“我”本质上也是孤独的,通过和妮基的相处她意识到虽然自己一直对这个国家向往且扎根多年,但是依然是一个异类,具有文化的隔阂。这个国家的现代人想用自己不愿想起的过去作诗,这个国家的丈夫膜拜自己一直想摆脱的文化,她和景子一样,母国的根一直纠缠在她们的血液里。不同的是,景子用自杀的行动符号化地展示了“异国风情”,“我”只能在故事中里找回自己。
在景子短暂的生命中,“我”和她像两棵彼此孤离兀立的树,但在异国泥土的覆盖下,她们的根伸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她们把根纠缠在了一起。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7
读完这本书已经很久了,现在甚至忘记了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但记得主题是关于忏悔。得知这本书是诺奖得主的作品,我更加充满期待。但整体看完之后,有种被骗的感觉。仿佛准备盛装出席一次宴会,一心要艳压群芳,结果去了才发现其他人都是随意着装。自己不仅不合时宜,还有一丝失望。此前,我在阅读本书之前,知晓作家国籍之后,我会为他烙上一个标签:日本作家。我所了解到的日本作家是川端康成那一代的,正如川端自己所说,他致力描绘的是二战后日本破败山河下的残照之美。因此,我在未阅读本书之前,以为日本作家的行文该是淡淡的悲伤与中国古诗式的含蓄,川端笔下的雪国美丽、哀伤而又易碎,它美的让人心碎,更多无法言表的东西像一首诗一样从心间流淌,它太美了,美的让人自惭形秽。以至于后来我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时,总是被这个影响左右。日本的作家天生都带着点忧郁,这其实也算是一块短板,我见识了一根胡萝卜,总不可能指望所有的胡萝卜都是这个样子。
但在这里,我想说明的不是石黑写的不如川端,也不是呼吁人们去读川端的书,当然他的书确实该细细品读。但我更想说明的是,如同时间的匆匆流逝,那种川端式的优美文风与淡淡的忧伤或许正被另一种东西取代。我失望的原因也在于此:哀叹自己曾经欣赏过的,无奈即将到来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世界静止不变,就会变成一滩永不流动的死水,变化是无可厚非的,我既赞美曾经也拥抱将来。同时,我发现这本书中属于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而属于日本的东西越来越少,这也是让我最惋惜的一点。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我不知道这样的趋向是好是坏,但我仍旧自我的醉心于川端那一代作家的文字。他在描绘的是日本人,而非人性,石黑更倾向于是探讨人性的问题。(这可能也与石黑是日裔英国作家有关。)相比较于文中的主线,我对文中所涉及的一对父子的相处态度更感兴趣,因为我感觉的这时的故事属于日本。我承认民族文化要向世界传播,须得找到与其他民族的共通之处,但这个世界文化又是以哪种民族的文化为标准呢?如果真的属于世界,民族文化之间可能会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世界化,我不太喜欢天下大同的文章,更希望带点民族特色,哪怕你跟我讲一个西方吸血鬼的故事我也乐意听,而不愿意去听那些虽然正确但乏味的大道。这种情形在以前也有过,莫言得诺奖的作品是《蛙》,但我老师向我们推荐过莫言的《生死疲劳》,我看过后也觉得写的不错,因为后者属于中国的东西很多,开卷即知这是中国作家写的书,这样满溢着本土情怀的书让我百读不厌。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可我依旧喜欢独具民族特色的东西。香奈儿女士和她创造的品牌如今享誉世界,也正是她一番话启发了我:身为女人,你可以没有奢侈的名牌衣服,也可以没有多余的资金与时间花费在打扮自己身上,但你必须有一件不能丢弃的衣服,那就是自我。这也是我对文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坚持身为一个作家的本心,坚持自我,全球化虽然不可避免,但文学总归得为人们的心灵留一方净土。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谈过,他不喜欢让人越看越烦的小说,而现今中国这样的小说却有很多。儒家思想浩大,无法求其全貌,我抓其凤毛麟角,总以为作家该是一个君子固穷的职业,太喧嚣或者太过亲近政治都没有什么好处。朋友说我有时候写文章离题离的厉害,但管他呢,我写的只是一己之感想,又不是千秋万代流传百世的圣人言,表达一个小老百姓的看法,这样也足够了。关者自己取舍吧。
远山淡影读后感篇8
读完《远淡影》后,脑海里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尽管作者叙述了"我"回忆起一久远的往事,在主人公"我"的叙述和思考中提供了直观外的线索,但那也只是片断的内容,就连那往事也是,此时此刻也是。于是,合上书,我仿佛置身于一片茫茫的原野,那里绿草如茵,陆离的花丛从我的脚下延伸,从平缓的丘陵背面一直到画卷的最远端,那里崇叠岭,高高的杉木从整齐的树林里的一个尖角,就像传统建筑的屋顶上的翼角,一切笼罩在一层灰色的氤氲之下,宛如阆苑仙境。造成这种错觉抑或说是遐想的原因恰是隐去了其形体,而留下简单的轮廓与淡淡的影子,空白处自然的会由想象力填充。
作者是以第一人称写作,但也只局限于"我"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叙述的角度不超过"我",没有多余的旁白(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但极少)与心理分析,仅有的猜测与所思同样拘于纯粹的"我"之内;其次,作者及"我"只着眼于眼前看到的、发生的和回忆的,而这些事没有龙去脉,于是,就造成一个不完整的印象,就像不断延绵的脊被画卷两端突然的拦腰折断;最后,尽管印象是不完整的,但作者有意提供断断续续的线索并让它们产生联系,让空白不是那么的空白,而是留下浅浅的灰色,正如到小说结束为止,对于景子是这个人的印象都是残缺近乎了无的,但相较于小说肇始——只告诉了景子的自缢以及纯日本血统——我们慢慢了解到了,景子名字的由、景子的出身、早年的生活环境、以及她音域的性格等,景子便是这远淡影,空白处则是她为什么要自缢。之外,还有"我"、长崎的阴影和万里子的去向一并构成了漶漫的群远景。因此,我十分的佩服作者的自制力与忍痛割爱的决心。
比较有意思的是,作者从一开始就提到景子的死却不打算描写这事对"我"内心造成如何巨大的波澜,转而回忆起有相似命运的佐知子,而通过佐知子的冷漠映射了"我"的冷漠,直到最后尽管感情有了起伏,在景子曾经的房间流连,但仍然能够感受到"我"身上的冷漠,于是浅层的冷漠与深层冷漠、现在与过去构成了画卷里的近景清晰与远景模糊的照片聚焦后的效果。另外小说中的每次对话总是会在某一句话上重复几遍,就像荡漾在旷谷间的回音,加深了距离感,从而在声音上也加强了淡薄感。
不得不感喟石黑一雄的技巧纯熟。